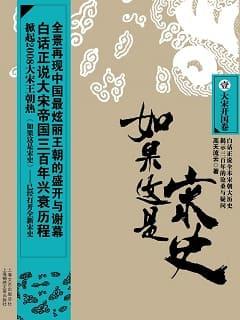- [ 免费 ] 第一章 前因――我本乱世一根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章 冻不死的种子
- [ 免费 ] 第三章 皇帝流水线
- [ 免费 ] 第四章 让天下人都签投名状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章 一个员工是怎样折磨自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章 天下英雄他最强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章 冯道之殇
- [ 免费 ] 第八章 第一战将赵匡胤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章 陨落的太阳
- [ 免费 ] 第十章 机关算尽伤聪明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北宋诞生记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请注意,现在我是皇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我的江山我装修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我有一个梦想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六十六天平后蜀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胜利者的规矩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爱我的间谍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啊……天杀的城墙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宋朝的内核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对这个杂种要毫不留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寄生胎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 我的名字叫李煜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三章 五字错千年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四章 烛光摇曳话当年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五章 魂归洛阳川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章 天下不过二三事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章 春水向金陵
- [ 免费 ] 第三章 命运之巅 睥睨天下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章 如果这是契丹
- [ 免费 ] 第五章 一夜梦燕云
- [ 免费 ] 第六章 剧痛的心灵
- [ 免费 ] 第七章 所谓名相
- [ 免费 ] 第八章 百年之错
- [ 免费 ] 第九章 天国逆子
- [ 免费 ] 第十章 契丹,朕赌你的全部!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大宋名相第一人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痛烈人生 屹立不倒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生死万岁殿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啊……衰神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温暖贴心王爱卿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开业大吉 昏天黑地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李继迁时刻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我寇准又杀回来了!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豺狼的末日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天不灭赵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澶渊……澶渊!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 天书降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三章 圣祖临
- [ 免费 ] 第二十四章 大宋官场众生相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五章 宋朝的味道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章 宋朝能否不姓赵 ...
- [ 免费 ] 第二章 老冤家寇准、李迪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章 赵恒建陵
- [ 免费 ] 第四章 丁谓的高度
- [ 免费 ] 第五章 生死两艰难
- [ 免费 ] 第六章 三国少年说
- [ 免费 ] 第七章 宋朝边帅曹玮
- [ 免费 ] 第八章 赵恒刚登基
- [ 免费 ] 第九章 王钦若之死
- [ 免费 ] 第十章 太后的幸与不幸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祭天祭祖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怨恨变毒药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吕夷简做到了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妈妈,我想你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一份超级荣誉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西夏孵化记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史上最隆重离婚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废后自有故事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楷模赵光义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开封青云路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不能打压,试试贿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 三百年间他第一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三章 范仲淹和他的朋友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四章 党项人的发家史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五章 谁是首相
- [ 免费 ] 第二十六章 黑暗前的黎明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七章 必胜的信号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八章 李元昊的痛苦——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九章 士兵们的潜台词 ...
- [ 免费 ] 第三十章 超级绝望的现实 ...
- [ 免费 ] 第三十一章 勇气和力量 ...
- [ 免费 ] 第三十二章 悲怆好水川 ...
- [ 免费 ] 第三十三章 胜败能论,只是枭 ...
- [ 免费 ] 第三十四章 一大群的牛马驼羊 ...
- [ 免费 ] 第三十五章 战士和平民,有本 ...
- [ 免费 ] 第三十六章 小结
- [ 免费 ] 第一章 位高权重
- [ 免费 ] 第二章 叱咤风云
- [ 免费 ] 第三章 平息国内叛乱
- [ 免费 ] 第四章 红黑脸待遇
- [ 免费 ] 第五章 狡诈贪婪
- [ 免费 ] 第六章 背叛的迹象
- [ 免费 ] 第七章 传说
- [ 免费 ] 第八章 得到暗示
- [ 免费 ] 第九章 极度愉悦
- [ 免费 ] 第十章 帝国首相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经典时刻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开山之作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君子不结党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高雅纯洁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干掉叛贼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国运分水岭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威严和力量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解燃眉之急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典型的官员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皇帝的特权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燃烧的火鸟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 贝州之赏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三章 官场琐事
- [ 免费 ] 第二十四章 开天辟地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五章 阴性之水
- [ 免费 ] 第二十六章 中国神话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七章 曝光的事件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八章 帝国的唯一继承人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章 宋朝病人
- [ 免费 ] 第二章 病情加重
- [ 免费 ] 第三章 强烈回忆
- [ 免费 ] 第四章 太后撤帘
- [ 免费 ] 第五章 公子绝迹
- [ 免费 ] 第六章 公开争斗
- [ 免费 ] 第七章 惊天龌龊
- [ 免费 ] 第八章 流云方寸间
- [ 免费 ] 第九章 法儒不同炉
- [ 免费 ] 第十章 指点江山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千年疑团说青苗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多面司马光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士大夫阶层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东明县事件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北宋三人行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冏之王唐坰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异域铁血铸辉煌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王安石罢相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人只为己,天诛地灭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辽国分水岭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习惯性诬陷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 陌上花落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三章 巅峰悄然退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章 飞扬的梦
- [ 免费 ] 第二章 俺是兵部的
- [ 免费 ] 第三章 最伟大西征OR最沉痛西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章 真宗朝的秦翰
- [ 免费 ] 第五章 投降
- [ 免费 ] 第六章 扒开黄河
- [ 免费 ] 第七章 必须冲击三次
- [ 免费 ] 第八章 10万军中取主将人头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章 昼夜不停
- [ 免费 ] 第十章 如此一生,复有何求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物资基础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这是强人手段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圣人PK文豪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毁灭北宋的种子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高滔滔摆乌龙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何以清算,唯有凶残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西线百年第一人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熙河军姚雄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太后英明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同文馆之狱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 与弗取,反受其咎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章 天命
- [ 免费 ] 第二章 宋朝的兰花
- [ 免费 ] 第三章 北宋终结者
- [ 免费 ] 第四章 党争养蛊孰为殃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章 国之少年
- [ 免费 ] 第六章 隐相大人
- [ 免费 ] 第七章 疯狂的石头
- [ 免费 ] 第八章 神仙大卖场
- [ 免费 ] 第九章 永远的西军
- [ 免费 ] 第十章 公元1111年的卢沟桥事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完颜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流散的镔铁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海上之盟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灭国级蛀虫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青溪县的真相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燕云梦魇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如此复燕云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欢呼,灭亡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靖康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东京保卫战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钦宗式沉沦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 烈日骄阳,男儿雄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章 血色黄昏
- [ 免费 ] 第二章 如果还有明天
- [ 免费 ] 第三章 何至于靖康
- [ 免费 ] 第四章 审判日众生相
- [ 免费 ] 第五章 赵构集结号
- [ 免费 ] 第六章 皇帝替代品
- [ 免费 ] 第七章 宗泽,过不去的河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章 建炎南渡
- [ 免费 ] 第九章 搜山检海捉赵构 ...
- [ 免费 ] 第十章 永远的西军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铁血和尚原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金归秦桧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西南决战仙人关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河朔岳飞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冠绝天下、梦回万岁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光荣北伐,洛阳城下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淮西军变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沉默的铠甲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英雄的黎明
- [ 免费 ] 第一章 顺昌血战
- [ 免费 ] 第二章 岳飞第四次北伐 ...
- [ 免费 ] 第三章 踏破贺兰山缺
- [ 免费 ] 第四章 十年之力,废于一旦!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章 岳飞战场受排挤 ...
- [ 免费 ] 第六章 赵构秦桧耍阴谋收兵权 ...
- [ 免费 ] 第七章 岳飞之“罪”:莫须有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章 天日昭昭!天日昭昭! ...
- [ 免费 ] 第九章 一把手和二把手的明争 ...
- [ 免费 ] 第十章 死亡的泥潭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完颜亮很忙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完颜雍杀死完颜亮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南渡以来仅见的锐气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雍熙北伐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最传奇将军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宿州七日,血流成河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男儿到死心如铁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亡国之象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成吉思汗登上舞台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赵构终于死了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十年主角李凤娘 ...
- [ 免费 ] 第一章 梦魇江南
- [ 免费 ] 第二章 两朝内禅
- [ 免费 ] 第三章 韩国戚与赵皇亲 ...
- [ 免费 ] 第四章 宰相飞头去和戎 ...
- [ 免费 ] 第五章 蒙古史诗
- [ 免费 ] 第六章 西北落日
- [ 免费 ] 第七章 一战江山野狐岭 ...
- [ 免费 ] 第八章 天亡此仇
- [ 免费 ] 第九章 西域传说
- [ 免费 ] 第十章 最愚蠢权臣
- [ 免费 ] 第十一章 最成功权臣
- [ 免费 ] 第十二章 李全之殇
- [ 免费 ] 第十三章 亡西夏
- [ 免费 ] 第十四章 百年最强了无痕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五章 端平入洛
- [ 免费 ] 第十六章 南方天空最后一抹晚 ...
- [ 免费 ] 第十七章 阎马丁当,国势将亡 ...
- [ 免费 ] 第十八章 云南桃源
- [ 免费 ] 第十九章 上帝折鞭处
- [ 免费 ] 第二十章 暮色襄樊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一章 伯颜下江南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二章 一片降旗出临安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三章 千古悲恸难言处 ...
- [ 免费 ] 第二十四章 崖山之后看中华 ...
杏书首页 我的书架 A-AA+ 去发书评 收藏 书签 手机
繁
第二十三章 官场琐事
2018-9-26 21:22
放下狄青,让我们跳出仁宗朝超长超烦乱的官场琐事,跳到开封城的高空里,向下俯览,去寻找当年国家大事的主线,来发现宋朝的国运秘密。
它是怎样兴旺的,又是怎样衰败的。针对于这时,矛盾和变数就都集中在了至和、嘉祐年间(公元1054-1063年)。这段光阴,是北宋史上罕见的国泰民安、岁月平和的年代,它让后世人不断地追忆怀念,恨不能穿越时空,永远停留在那时。
中国人印象里名人辈出,繁华似锦,悠游享乐的岁月,指的就是这时。精确计算,狄青升为枢密使,就是在这前一年。之后好事继续上演,两个月后,最牛最强硬的言官唐介也回京了,他仍旧担任御史。一切的迹象都表明,仁宗皇帝想再次振作,让国家在灾难不断,反叛不断的局面里兴旺起来。
这多好,可惜天不从人愿,赵祯的悲哀突然降临,他最心爱的人死了。皇祐六年(公元1054年)正月初八,张贵妃暴病身亡,年仅31岁。从这时起,仁宗皇帝的神智和身体都大受打击,他承受不了心爱之人的离去,逐渐变得精神恍惚,沉默不语。
历史到了这一步,史书上的记载就变得非常妙微,作为现代人和作为宋朝人,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。说宋朝的官场,张贵妃之死,让他们非常高兴。我没有夸张,说的不是特指包拯在内的言官系统,指的就是宋朝的全体官场。
张贵妃之死,让所谓的张氏集团骤然崩溃,没有了枕头风,看看张尧佐、文彦博之流还怎么升官发财,尸位素餐。这真是大快人心,从此世界又变得公正了!至于皇帝本人的感觉如何嘛,就不是他们的业务范围了,在所有用儒家学说培养起来的官员的认知系统里,人活着,有“礼”这种法规来规范着,人死了,同样也有各种相应的标准去埋。
悲伤?那好办,您可以用辍朝了,成服了,追赠了之类的办法来表现。一切都有制度,保准您生荣死哀,风光体面。
于是他们就愤怒了,真是搞不懂,皇帝怎么能这样出格呢?!赵祯给自己的心爱的女人的出殡礼仪定在了最高规格上。
居然是以皇后之礼殡葬!
严格说来,他这样做是有前科的。当年被他废掉的郭皇后暴死,他也以皇后之礼发送,完全不顾刚娶进门的曹皇后是什么感想。可那时情有可原,毕竟郭氏曾经母仪天下,除去“耳光门”事件外,没有任何出错的地方。这时的张氏完全不能等同,一介贵妃而已,并且时常干政,受贿的丑闻都牵扯到了当时的宰相加御史中丞等等等等一大堆高官。
还有她不当宰执死不甘心的伯父。这样的女人,不打进冷宫都是便宜了,凭什么再追封成皇后?
赵祯不管这些,不管谁反对,他一意孤行。在张氏死后的第四天,追赐其为“温成”皇后,在皇仪殿为其举丧,辍朝七日,天下禁乐一月,他本人亲自成服,到了发丧的正月二十日,率领文武百官,护送灵位出宫,进奉先寺。
这一切的规格,是无可挑剔的皇后丧仪,说句实话,就连当年他的养母刘娥皇太后都没能享受着。本来注定了只能给一个女人预备着,就是现东宫之主,曹皇后。可是她又消失了,历史里没有她这时的记载。这位贤德倒成了习惯的女士继续沉默。可她应有的权力自然有别人为她维护。
维护行动分为丧前和丧中。
丧前时,为了皇后的头衔,整个御史台在现任中丞孙抃的率领下全体出战,和皇上闹得你死我活。半点都没有夸张,因为事后皇帝没妥协,他们真的全体辞职,撂挑子不干了。
丧中时对抗进入高潮,就在举哀的最重要时段,为死者正名,读哀册时,出了大娄子。原先指定的枢密副使孙沔突然放下了哀册,说:“当年章穆皇后葬礼,是由两制官(翰林学士、知制诰)读哀册。现在温成皇后是追封的,反要两府大臣行事。这与礼不合,臣拒绝读册。”
事发突然,皇上和大臣们都愣住了。这个孙沔是狄青南方平叛时的副手,很听话的一个人,尤其是刚刚提拔上来,正应该百依百顺报答皇恩的,怎么会突然间翻脸?
赵祯惊怒交集,但是为了葬礼顺利进行,为了让心爱的女人得到最后的安慰,他忍住了,反而派人好言相劝,孙爱卿,你就读了吧。
孙沔大义凛然,说了一句话。“以臣孙沔读册则可,以枢密副使读册不可!”说完把哀册往桌子上一放,没向任何人请示,自己就退了下去。
彻底冷场了。赵祯望着眼前黑麻麻站满庭院的大臣,只觉得一阵阵的头晕。他今年45岁了,自13岁登基以来,已经称帝32年。近半甲子的光阴里,可以说对臣子们超级仁慈。他曾经在后花苑里游玩,嫔妃云集,侍者成群,他边走边频频回顾,像是寻找什么,却始终没说出口。直到回到宫里,才急匆匆地说取水来,这一路快渴死了。
嫔妃们很不解,官家为何不在外面要水,弄得渴成这样?
他苦笑了一下,说回头了好几次,都没看见随侍奉水的人。如果当时要水,管事的人岂不要受现难?所以忍一下吧,直到回到宫里。
更有一次,他半夜忽然想吃烧羊肉,想了又想,还是硬压了下去。旁边人问为什么,他说,一旦他想吃,就会变成惯例,每天晚上御厨房里都会杀羊准备。天天杀生害命,于心何忍?
这样的事很多,对眼前这些大臣们,他更加是轻拿轻放,平时的俸禄厚上加厚就不用说了,就算是犯了大错,也没有一棒子打死,永世不得翻身的例子。这样的好,为什么就换不回来些许的同情和理解呢?
近在咫尺的这个女人,不管她之前做过怎样没有分寸的事,她都陪着自己度过了之前战争动荡,反叛不断,党争烦人的日子。大臣们,你们道貌岸然、圣人嘴脸,难道身上就真的一点污点都没有吗?抛开平日里工作之余到各处勾栏里公然鬼混,其他的丑行更是数不胜数。
就以孙沔你为论,就不是个好东西。
孙沔贪财好色。按说只要是男人,就没有不好这两样的,可像他这样出格的也实在不多。总体来说,他做到了到处好色,随地发财,走一路贪一路,从没有落空的时候。
先说财,他在并州当官时,衙门里的吏卒们时常出公差,四面八方,跑得超勤快。却不是为了公务,是拿着朝廷的旅差费,给孙沔贩运纱、绢、丝绸、纸还有药品。这很让人讨厌,不过是当时的风气,几乎每个官员都搞这样的把戏。
同时过百万的禁军、厢军,各衙门的小吏衙役们也就都有了营生,不至于太闲了。
上面的是通例,下面就刺激了。孙沔贪财时是凶狠型的,只要挡了他的财路,不管是谁,都小心着家破人亡。他在杭州当官时有两件事,很有代表性。
首先是继续做买卖,孙沔亲自出马,和一个姓郑的萧山人谈纱的价钱。郑某一时不识官商真面目,出的价很高,而且不还价。孙沔只好怀恨出门,越想越气,决定来个狠的。他派人去查郑某的案底,辛勤查账之后,果然查到这人偷漏了税。
把柄在手,价钱好说。可惜郑某把事儿看得太轻了,孙沔要他的纱,更要他的命,一点偷税的勾当,就把他发配到了别州,家产全部充公!
这还是勉强说过去的事,毕竟郑某自己手脚不干净,给孙沔留下了整人的理由。下一件事,就纯粹是恶人本性,卑劣的畜生行为了。
杭州自古繁华,地杰人灵之外,还相当的有钱,民间总有些稀奇古怪的宝贝偶尔曝光。杭州市民许明就藏有100颗成色极好,浑圆硕大的珍珠,以及一幅郭虔晖所画的《鹰图》。地道的奇珍加古董,让懂行的孙沔大流口水。为了得到这两样东西,孙沔大动了一番脑筋,想出了一个层次分明,超级混蛋的计策。
东西有两样,要各个击破。谨防许明一时冲动,把宝贝毁了,来个玉石俱焚。他由自己的小舅子出面,先去买珍珠。100颗罕见的大珍珠,他出价32000钱,也就是320贯!几乎连一颗珍珠都够戗买下来。但是竟然成交了。
这就是手段的高明。孙沔摸准了许明的心理,许明爱珍珠,更爱《鹰图》,总想着花些代价把瘟神打发走,所以对珍珠就不会认真。
珍珠之后,《鹰图》就更成了许明的命根子,孙沔知道得玩狠的了。现在请朋友们掩卷默想,要用什么样的手段,才能让许明乖乖地交出宝贝,不得不屈服呢?
千年之后,都觉得匪夷所思。孙沔居然查到了许明小时候有个乳名,叫“大王儿”。这就是罪,一介平民,僭越称王,你想造反吧!
许明被刺配充军,《鹰图》顺利落到孙沔手中。许明直到孙沔调离杭州之后,才在营牢里自断一臂到提点刑狱使司喊冤,得到释放。
以上是孙沔的贪财事例,下面看他的好色。
孙沔之好色,达到了兼收并储,来者不拒的程度。具体的表现就是无论是良家妇女,还是军营官妓,只要他看上了,就在劫难逃,终究到手。
他在处州当官时,某次外出游玩,偶遇一位名叫白牡丹的女子,突然心动,不可抑制,于是诱(史书原字)回官舍,如此这般。这是第一件,第二件发生在并州,他在上任的路上,居然公开接收妓女一路同行。
以上考虑到被害方的身份,妓女,还有白牡丹这个名字就不是正当职业者,孙沔的行为只能归纳到行为不端上,小小的风流罪过。那么请看下一例。它也发生在风景如画的杭州。
杭州自古多美女,西湖边上总关情。孙沔曾经日夜都在那里流连。结果他就看到了一位姓赵的超级美女。可惜名花有主了,她许配给了一个叫莘旦的人。孙沔开动脑筋,要怎样才能不合理但绝对合法的把赵美女据为己有呢?
办法永远都会有的,只要你有权力和欲望。孙沔先从莘旦的家人下手,他借口莘旦的母亲与和尚私通,把她抓到官府。又指派官妓把赵美女的妈妈看住,另换一套面目,充当救命恩人,把赵MM带走,从此日夜厮守……这就是在张贵妃葬礼上大义凛然,主执正义的枢密副使孙沔孙大人的真实本色。
这样的人居然能位极人臣,还动辄以仁义道德自称,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。其实也不止是他,全宋朝官场的大臣们,几乎全体手脚都不干净。就以这次葬礼风波为局限,把出风头的几位都详述一遍,就可以看到盛世间的士大夫一族是怎样的嘴脸了。
下一位出场的人是宰相陈执中。前面说过,庞籍下野之后,梁适升相,但他没有资格做独相,很快皇上的老师、恩人陈执中回朝,分了他一杯羹。这时孙沔突然当众秀道德,撂了挑子,危难中陈执中顶了上来,坚决支持皇帝。
枢密副使不读哀册,那么宰相来读。陈执中让张贵妃的葬礼骤然升格,比之前的待遇更高了。葬礼圆满结束,皇帝对恩师充满了感激之情,大臣们恨不得骂死这个老牌的墙头草。
这是士大夫之间的仇视,作为现代人,可以忽略,因为陈执中毕竟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,按照宋朝的为官之道做人。我们所要看的,是他作为一个“人”,做出了什么样的勾当。
半年之后,他家里出了件事。官方资料记载,是死了一个婢女,名叫迎儿。遍体鳞伤,体无完肤,开封府调查,是被活生生打死的。案发过程,有两个说法。一,是陈执中亲自动手,把婢女打死;二,是他一向酷虐的爱妾张氏殴打至死。
官方结论,不管是哪一种,陈执中都有不可推卸的现任。
还有另一个版本的记载,出自司马光的私人笔记《涑水记闻》,死的不是一个婢女,而是三个。迎儿当年只有13岁,只是个女童而已,不知犯了什么过错,在张氏的鼓动下,陈执中亲自动手,毒打多次,寒冬天气里,赤裸捆绑,关在黑屋子里,直至冻饿而死。另两个女婢一个叫海棠,另一个不知名,海棠被打死,无名的那个被剪成秃发,自己上了吊。
这是堂堂宰相府,知礼读书家的做的事吗?!陈执中对外恭谦礼让,对谁都客客气气,想不到背地里居然这样残忍刻毒!
事情曝光了,陈执中被御史台弹劾,停职回家待罪。从当时和现在人的普遍意识里,他这就算完蛋了。想想看在宋朝的仁宗年间,居然出了这样的事,除了法办之外,还有别的答案吗?结果是有。那是个封建年代,人和人就是不平等的,现代的人权意识,在那里没有市场。
哪怕是仁宗皇帝再仁慈,也没法把一届宰相和几个丫鬟使女的性命等同起来。他犹豫,这只是私事,最多不过是丑闻,难道就此罢免老恩师,甚至法办他吗?
他的这种犹豫,直接导致了司法部门对陈执中案件的审理力度。尽管御史台全体出动,不断弹劾,陈执中的宰相头衔岿然不动。直到仁宗朝第一位吵架王、弹劾王欧阳修回京。
庆历年间被贬到外地的大才子欧阳修终于回来了,他的职务被安排到一个非常对口,非常称职的地方,是两制官里的翰林学士。清闲又富贵,可他待不住。第一时间地冲进了漩涡,不遗余力地打压陈执中,不把这个貌似忠厚,极端无耻的斯文败类打倒斗臭,他誓不罢休!
至于为什么这么冲动,他自己知道,全宋朝也都知道。那涉及到另一个巨型丑闻,间接地就由陈执中制造。
庆历新政时欧阳修比范仲淹等主角还要出彩,他旋风腿冲天炮打遍宋朝每一个角落,让几乎全体官员都灰头土脸贴上小人的标签。这样做是有报应的,牛人出牛事,仁宗朝、甚至北宋第一丑闻就落在他的身上。
事情是这样的,欧阳修的二妹夫早死,妹妹带着女儿张氏到他家生活。欧阳修把外甥女养大成人,嫁给了自己的远房侄子。可是他的教育力度明显不够,这位张氏女孩儿有个坏习惯,她喜欢外遇,和丈夫衙门里的办事人员有了暧昧关系。事发之后,由当时的开封府尹杨日严办理。
杨日严在历史里籍籍无名,在欧阳修的心里也就没了印象。他狠扁过的人实在太多了,数都数不过来。这位杨先生曾经在益州任上贪污渎职,被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弹劾丢官。有怨报怨,有仇报仇,本来是小一辈的龌龊事,竟然联系到了老一辈的欧阳修身上。
审理报告上说,张氏供认,当年在欧阳修的府上,她和舅舅通奸,而且有银钱往来。此报告一公布,天下立即大哗。天哪,这是乱伦,最让人不齿,最恶心的一种丑事,居然发生在了当代才子之冠的欧阳修身上!
会是真的吗?普天下的人都在问,官场上却一致认定。真的。理由有二,第一,欧阳修有前科,这人风流好色,早年时就和官妓鬼混,留下了好多精妙绝伦的诗词,他推都推不脱;第二,他变卖了张家的宅院,钱都归为己有。这有契约为证,根本无处抵赖。
在当时,舆论说什么的都有。有认为欧阳修被陷害,这是打击报复。不能说有银钱往来就是通奸吧?亲戚家互相借贷,这再正常不过了。都是杨日严这小人在从中搞事。另一种占绝大多数的说法是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,种种迹象表明,欧阳修就是个乱伦犯!
结果他就被贬出京师,外地反省了。要指出的事,那时的宰相就是陈执中,倒修事件中,他最差也是个默许者,所以欧阳修把他恨得死死的。这时丑闻轮流转,今年到陈家,还不快意报复?
欧阳修出手,是北宋仁宗年间最可怕的弹劾武器,堪称战无不胜,弹无不倒。从战绩来说,别说是软柿子陈执中,就连名垂千古,铁脸无情的包拯,都不在话下。
陈执中倒了,他熬过了整个御史台的狂轰乱炸,连御史中丞孙抃为了他辞职不干,要同归于尽都安然无事,可是欧阳修一到,立即被赶出京城,到亳州去反省思过。
事情到这里可以暂时告一段落。总结一下,在一般的史书中,这段时光里宋朝发生的都是一些零碎的琐事,没什么需要重视的,也没法归纳出什么。紧接着它就进入到了至和、嘉祐年间(1054-1063年),那时就更太平,更祥和,更琐碎了。根本没法整体说事。
但是仔细研究,我发现不尽然。上面所说的这几件事,正是宋朝,至少是仁宗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仁宗朝在此之前,尽管外患内乱不断,可是在赵祯的领导下,一切都平稳有序。在张贵妃死后,赵祯的心灵和身体都发生了巨大变化,这直接导致了他的施政纲领,还有领导力度。
宋朝开始变样了。
说张贵妃之死,本是一件小事,除了生死两皇后的名分很重叠,对曹皇后一再地轻视不敬之外,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?有的,自古以来,领导人的配偶对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巨大,连带着对国家的运作也有波及。远的例子,比如唐高宗李治,如果他的身体一直健康,怎么轮到武则天批奏章,管国事?近的说刘娥,赵恒晚年神智昏乱,没法办公,她才走上了前台。再近些说慈禧,她的丈夫也是病死得早,儿子还太小,才轮到她当政。
综上所述,已经很明确了。如果这几位女强人的丈夫一直健康正常,她们根本没有走出后宫,打家劫舍的机会。证据就是她们丈夫得病之前,她们没一个敢挑事的。
具体到赵祯的身上,就是张贵妃死了,他必须得找新的女人。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,更是工作的需要。他得给宋朝的百年基业生出个继承人来。于是女人多多选,出现了10位得宠的嫔妃,号称“十阁”。10个啊,这样的工作力度,让赵祯很快出现了健康问题。
先是无精打采,渐渐地病情加重,突然间昏迷不醒,长达3天。之后健康每况愈下,再也没有振作起来。这样导致了两个后果。
1,传说中的盛世出现了。国家随遇而安,官员随国而安,和他的身体一样,平稳高于一切。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,做到了与民休息;
2,传说中的名臣出现了。皇帝病倒,国家还得有人管理,一大批的名臣冒了出来,他们既要照顾好皇帝,又管理好国家,这让所有朝代的臣子们钦佩,造就他们不灭的英名传奇。
具体的发展过程,就从陈执中下课开始。他和梁适都走人,中书省大换血,上任的是文彦博和富弼。其中的富弼和稍后上任的权御史中丞包拯、任经筳侍讲的大儒胡瑗,以及翰林学士欧阳修,并称为“四真”。即富弼是真宰相、欧阳修是真学士、包拯是真御史、胡瑗是真先生。
至于文彦博,谁让他的仕途那么悠长,中间起伏不定,到评定四真的时候,他又潜水了,头衔被暂时剥夺。
四真当朝,是宋史里少见的盛世传说,被后世一再传颂,那么就从他们说起吧,看看这段时光都发生过什么事,谁做了什么。四人之中,胡瑗首先剔除在外。这位真先生是儒学宗师,除了学问高深之外,最让人敬佩的就是道德隆重。人家从来不趁着和皇上挨得近,就什么都讲,什么都掺和。
于是经书之外,没有天地。胡瑗独善其身。
包拯暂时也没有戏份出场,他之前弹劾张尧佐用力过猛,还在修养复原中。余下的就只有富弼、文彦博、欧阳修了。这三个人一贯活在风口浪尖上,可惜富弼也要除去,他真的成了仁宗朝的“真宰相”了。他创造了一个纪录。
高洁无瑕,片尘不染。终其一生,再没有任何人弹劾他。
这真是破天荒头一个,连范仲淹都做不到。其原因是什么呢,此人变了。被夏竦的谣言击中,贬出开封之后,富弼的心灵起了极大的变异,让当年那个为国为民热血沸腾,与契丹交涉不惜性命,谈改革不顾身家的真汉子变成了宋朝最经典的执政官,成为“真宰相”。
这个心灵转变,除了悲哀,或者成熟了、腐烂了之类的评语之外,其转变的原因、过程,都足以成了宋朝不断没落,走向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那个冬天的缩影。帝国之亡,实亡于人心之没落。
说得远了些,五人中只剩下了欧阳修和文彦博。这两个人都是新回京师,能力和风格让他们立即就成为风云人物,其开端就是困扰了宋朝快八年的黄河水灾。
八年前黄河改道,按中国5000年里只有8次的概率,可以说是近千年一遇的大灾了。面对滔天的洪水,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,还有巨大的损失数字,宋朝的举措是相当认真的。
前面说过,两位前宰相贾昌朝、丁度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如贾氏的恢复故道,商胡溃堤,就在商胡复原;丁氏的从长计议,先疏通河水,看准流向之后再动手的缓期救灾。怎样决策,慎之又慎,认真的程度达到了连续思考了4年。
4年后,公元1051年七月,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又决堤了。
这次决堤就像是得了癌症之后又发了次小感冒。尽管癌症很要命,可是感冒来得更现实,让人没法不先治它。5个月之后,郭固口合拢,但是仅仅限于合拢。水道内淤泥堆积,越来越厚,水面被抬高,随时都有漫过堤坝,再次崩溃的危险。
说到这里,就让人奇怪了。宋朝是中国历代最有钱的王朝,就以贾昌朝恢复故道的办法,号称最废钱费力,也不过就是1000万贯钱,10万民夫而已。参考一下历次战争的花费,就该知道,这不过是宋朝的九牛一毛。那么拖来拖去的,到底因为什么?
谜底还得再等一会儿揭开。进入至和年间了,文彦博和富弼当上了宰相,这两个人不管真实面目与传说中有多大的差距,为国为民的好心肠还是有的。他们广泛征集意见,整理出了一个新办法。据专家判断,一旦实施,就能以最小的工作量达到最完美的治水效果。
――六塔河方案出笼。
六塔河,在河北省清丰县的六塔镇,与黄河相通,却不入海。具体的办法是,把六塔河的河面河道加宽挖深,来容纳黄河泛滥的洪水,这样上游的商胡地段就会得到缓解。水流减缓之后,商胡的崩溃点就可以相当容易地塞住,同时约束河水按故道流淌,进入大海。
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宋朝的河渠司主管李仲昌。从身份上讲,这是位专职专管的治水专业人员,说的话应该靠谱。从纯技术上分析,也很有道理。以六塔河分水,可以让商胡口的决堤处减缓灾情,容易堵塞。尤其是一旦成功之后,六塔河的后期作用更是巨大。
它可以成为黄河的永久性分水道,不管在什么时候,都能保证黄河的崩溃系数维持在之前历代最低的程度。多好的办法,立即就把文彦博和富弼给迷住了。他们联名上报给皇帝,请批准,立即实施吧。
且慢,欧阳修有话说。
新任的翰林学士看上去义愤填膺,心里有好多的话,都快把他憋爆炸了。他一口气写了几千个字的奏章,把前面提出的3种治河方案都批得体无完肤。
第一,关于贾昌朝的恢复故道,欧阳修指出,也不想想为什么近几十年来河患不断?就在于故道泥沙淤积,已经积重难返,根本就不可能再恢复了。一定要逆天行事,难道与天斗,真的其乐无穷?
第二,关于丁度的从长计议,就是宋朝版的官员不作为罪行。从长计议,8年了够长不?你有什么计议结果请尽快出现,难道国计民生的重要,都维系在您不定时短路的脑子?
第三,六塔河计划。这是最让欧阳修不堪忍受的,他实在是怀疑这个世界是怎么了,难道一个个国家大臣都成了白痴加废物?六塔河,只是一条40步宽的州县级河流,它能有多大的容水量,想让它给中国北方第一大河减水……你们的脑子进水了吧?!或许每个脑子注水100吨,黄河就安静了!
综上所述,每一条方案都不成立。欧阳修在愤怒之余,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。他建议派真正懂行的水利大臣到黄河的下游去,别再只把目光盯在商胡、郭固口等上游危险地段。把黄河的入海道路修好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
水往东流,渠成自畅。这才是根本正路!
又一个方案产生,欧阳修把整个朝廷吓了一大跳之后,又把希望给了他们。平心而论,他说得都在理,尤其是关于六塔河的分析。无论如何,40步宽的河面就决定了方案的先天不足。
那是给中原第一大河减水!
从理论上讲,只要六塔河的容积不够,黄河水势必倒灌回故道,上游的压力会急剧增加。欧阳修断言,那时上游必溃。
奏章交了上去,他和全天下人开始了等待。强调一下,这就是欧阳修的力量,他的文章在年轻时代就风行全国,20多年以后,已经是宋朝当时公认的文学泰斗。天下第一大家,随便写点什么都是万众瞩目,这种影响力谁敢忽视?
但真就被忽视了。欧阳修怎么也搞不懂,无论是治河的见解,还是文字的功力,还有他和富弼的交情,都注定了他将扭转治河事件的乾坤,可偏偏就被扔进了废纸缕里,没人去看。
李仲昌的六塔河计划被提上日程,变成了治河主旋律。
欧阳修再一次失败了,他像惯例一样的被主流官场所抛弃。这种遭遇从一些角度上看,是很好玩、很可笑的,他怎么总是出丑啊,干生气没办法。可换一种角度来看,就会别有一番感触。这件事起码潜藏着两个真相。
第一,历尽官场风霜,唯一没有变的人只有欧阳修。以还活着的庆历新政的“君子党”为限,富弼变了,韩琦变了,那些曾经激扬奋发的青年馆阁人员更是找不到踪影。只有欧阳修以前什么样,现在还什么样。这让他继续在官场上出丑,总是当异类。
可“道之所在,虽千万人吾往矣。”他坚守着从青少年时起就抱定的信念,虽然迂腐,哪怕不合时宜,他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上永远都保持着一个书生的本色,从来都只做他自己。这难道不是极端难能可贵的吗?
第二,他这次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。治河,至少在古代,从来都不是一件民生工程,而是一种政府工程。欧阳修与庆历故人们渐行渐远,不与同流,属于无党派人士了,那么自然就不会再有人重视他的意见。
三种意见,哪种都有幕后的支持者。贾昌朝的背后是陈执中,李仲昌的背后是文彦博和富弼。丁度的稍好些,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提出具体办法。
这样一件大工程,在谁的治下成功,都会变成他巨大的政治资本。就比如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法,他和陈执中都处在下野状态,如果被采用,现任的文、富二人脸往哪放?一旦治河成功,功劳算是谁的?
贾和陈立即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声望。
围绕着最后利益归属的问题,巨大的水灾危害变次要了。双方都用尽了手段,来打压反对对方的方案,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的意图得逞。最先发难的人是贾昌朝。
贾昌朝的资历很高,在庆历年间从右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,一路升上了参知政事,再到枢密使。直到新政开始,才被范仲淹、欧阳修赶出朝廷,也就在那时和富弼结成了冤家。这时他的运气非常好,本来国家重大决策,大臣们除了写奏章,搞辩论之外,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可是机会突然降临,让他能使盘外招了。
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春节时。宋朝的至和三年(即嘉祐元年,公元1056年)。正月初一,是一年中的大日子,这一天百官齐集大殿,盛装排列,庆贺元日大朝会。谁也没有料到,就这在这个时刻,出大事了。
只见两边的内侍把殿上的帏帘卷起,露出了帘后的皇帝,大家正要参拜,突然看见皇帝的头向一侧歪倒,随即整个人都倒了下去,皇帝昏倒了!
御阶上的帘幕立即又拉了起来,里边人影晃动,一阵忙乱。下边的百官们惊慌骚动,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样了。直到好一会儿后,帘幕重新拉开,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仁宗皇帝,他又能坐直了身子,与大家遥遥相对。
当天大臣们勉强压住心里的恐惧,向陛下依次行礼,徐徐退下。回去的路上,每个人都在想,皇帝到底怎么了,明天还能照常登殿理事吗?
明天不行,宋朝的年假直到大年初五。初五日上班,大家接着朝贺,而且有新节目。宋、辽两国乃兄弟之邦,每年春节,辽国都要来给哥哥拜年,于是按惯例,初五这一天,要在紫宸殿设宴,款待辽国使者。
全体朝臣都提心吊胆,要是陛下再当众玩次晕倒,这名声可就传出国界了。真的要变成“晕君”?他们多虑了,皇帝可以晕倒,不过得20年一遇。大初五的,仁宗有新花样。
简短节说,所有的排场重复了近100年,都成惯性动作了,什么错也没有,直到宰相和皇帝面对面。最高潮的桥段到来,得由宰相手捧酒觞登阶近距离为皇帝贺寿,并请皇帝发表新年讲话。
就见新年有新气象,陛下坐得稳稳的,下面群臣站得静静的,皇帝突然说,“不高兴吗?”(不乐邪?)文彦博一下子就愣住了,这句话什么意思?是陛下看我不顺眼,还是对宋、辽两国的邦交有了新的意向,要在朝贺日给辽人不痛快?
脑子里电光火石般地闪烁答案,可是都觉得不靠谱。理智告诉他,最贴近的答案就是皇帝还在晕,说的是病话。他作为宰相,就别跟着晕了。于是闭嘴,马上上菜,开吃!
当天的宴席上仁宗一直稳稳地端坐着,没再说话,甚至没有表情。直到典礼结束。大臣们一把冷汗拎着,总算松了口气。不过再次回家时,心里就都有了个问号,皇帝是病好了,还是更重了?
这事儿还真不好讲,瞬间晕倒和语无伦次,哪个都要命。
第二天才真正要命。中华上国,礼仪之邦,初五日是迎接辽使,初六还要送行。仍旧还在紫宸殿,原班人马继续喝。辽国的使者正在上殿,走到庭中央时,皇帝突然间喊了一句话:“速召使节上殿,朕几乎不相见!”
满殿的大臣集体一哆嗦,您是今天失忆,还是昨天梦游,把一整天的事儿都忘干净了?眼看着宋朝在外国人面前保持了近100年的体面就要倒塌,在场的官员们瞬间开始配合,兵分两路,台下面由宰相出头,把辽国使者拦住,直接往外拉。
理由是皇上高兴,昨晚上喝醉了,今天由大臣们在驿馆里设宴,咱们换台喝。
这时台上面一片忙乱,内侍太监们不由分说,把皇帝架起来就走。那架势倒真跟宰相说得差不多……
它是怎样兴旺的,又是怎样衰败的。针对于这时,矛盾和变数就都集中在了至和、嘉祐年间(公元1054-1063年)。这段光阴,是北宋史上罕见的国泰民安、岁月平和的年代,它让后世人不断地追忆怀念,恨不能穿越时空,永远停留在那时。
中国人印象里名人辈出,繁华似锦,悠游享乐的岁月,指的就是这时。精确计算,狄青升为枢密使,就是在这前一年。之后好事继续上演,两个月后,最牛最强硬的言官唐介也回京了,他仍旧担任御史。一切的迹象都表明,仁宗皇帝想再次振作,让国家在灾难不断,反叛不断的局面里兴旺起来。
这多好,可惜天不从人愿,赵祯的悲哀突然降临,他最心爱的人死了。皇祐六年(公元1054年)正月初八,张贵妃暴病身亡,年仅31岁。从这时起,仁宗皇帝的神智和身体都大受打击,他承受不了心爱之人的离去,逐渐变得精神恍惚,沉默不语。
历史到了这一步,史书上的记载就变得非常妙微,作为现代人和作为宋朝人,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。说宋朝的官场,张贵妃之死,让他们非常高兴。我没有夸张,说的不是特指包拯在内的言官系统,指的就是宋朝的全体官场。
张贵妃之死,让所谓的张氏集团骤然崩溃,没有了枕头风,看看张尧佐、文彦博之流还怎么升官发财,尸位素餐。这真是大快人心,从此世界又变得公正了!至于皇帝本人的感觉如何嘛,就不是他们的业务范围了,在所有用儒家学说培养起来的官员的认知系统里,人活着,有“礼”这种法规来规范着,人死了,同样也有各种相应的标准去埋。
悲伤?那好办,您可以用辍朝了,成服了,追赠了之类的办法来表现。一切都有制度,保准您生荣死哀,风光体面。
于是他们就愤怒了,真是搞不懂,皇帝怎么能这样出格呢?!赵祯给自己的心爱的女人的出殡礼仪定在了最高规格上。
居然是以皇后之礼殡葬!
严格说来,他这样做是有前科的。当年被他废掉的郭皇后暴死,他也以皇后之礼发送,完全不顾刚娶进门的曹皇后是什么感想。可那时情有可原,毕竟郭氏曾经母仪天下,除去“耳光门”事件外,没有任何出错的地方。这时的张氏完全不能等同,一介贵妃而已,并且时常干政,受贿的丑闻都牵扯到了当时的宰相加御史中丞等等等等一大堆高官。
还有她不当宰执死不甘心的伯父。这样的女人,不打进冷宫都是便宜了,凭什么再追封成皇后?
赵祯不管这些,不管谁反对,他一意孤行。在张氏死后的第四天,追赐其为“温成”皇后,在皇仪殿为其举丧,辍朝七日,天下禁乐一月,他本人亲自成服,到了发丧的正月二十日,率领文武百官,护送灵位出宫,进奉先寺。
这一切的规格,是无可挑剔的皇后丧仪,说句实话,就连当年他的养母刘娥皇太后都没能享受着。本来注定了只能给一个女人预备着,就是现东宫之主,曹皇后。可是她又消失了,历史里没有她这时的记载。这位贤德倒成了习惯的女士继续沉默。可她应有的权力自然有别人为她维护。
维护行动分为丧前和丧中。
丧前时,为了皇后的头衔,整个御史台在现任中丞孙抃的率领下全体出战,和皇上闹得你死我活。半点都没有夸张,因为事后皇帝没妥协,他们真的全体辞职,撂挑子不干了。
丧中时对抗进入高潮,就在举哀的最重要时段,为死者正名,读哀册时,出了大娄子。原先指定的枢密副使孙沔突然放下了哀册,说:“当年章穆皇后葬礼,是由两制官(翰林学士、知制诰)读哀册。现在温成皇后是追封的,反要两府大臣行事。这与礼不合,臣拒绝读册。”
事发突然,皇上和大臣们都愣住了。这个孙沔是狄青南方平叛时的副手,很听话的一个人,尤其是刚刚提拔上来,正应该百依百顺报答皇恩的,怎么会突然间翻脸?
赵祯惊怒交集,但是为了葬礼顺利进行,为了让心爱的女人得到最后的安慰,他忍住了,反而派人好言相劝,孙爱卿,你就读了吧。
孙沔大义凛然,说了一句话。“以臣孙沔读册则可,以枢密副使读册不可!”说完把哀册往桌子上一放,没向任何人请示,自己就退了下去。
彻底冷场了。赵祯望着眼前黑麻麻站满庭院的大臣,只觉得一阵阵的头晕。他今年45岁了,自13岁登基以来,已经称帝32年。近半甲子的光阴里,可以说对臣子们超级仁慈。他曾经在后花苑里游玩,嫔妃云集,侍者成群,他边走边频频回顾,像是寻找什么,却始终没说出口。直到回到宫里,才急匆匆地说取水来,这一路快渴死了。
嫔妃们很不解,官家为何不在外面要水,弄得渴成这样?
他苦笑了一下,说回头了好几次,都没看见随侍奉水的人。如果当时要水,管事的人岂不要受现难?所以忍一下吧,直到回到宫里。
更有一次,他半夜忽然想吃烧羊肉,想了又想,还是硬压了下去。旁边人问为什么,他说,一旦他想吃,就会变成惯例,每天晚上御厨房里都会杀羊准备。天天杀生害命,于心何忍?
这样的事很多,对眼前这些大臣们,他更加是轻拿轻放,平时的俸禄厚上加厚就不用说了,就算是犯了大错,也没有一棒子打死,永世不得翻身的例子。这样的好,为什么就换不回来些许的同情和理解呢?
近在咫尺的这个女人,不管她之前做过怎样没有分寸的事,她都陪着自己度过了之前战争动荡,反叛不断,党争烦人的日子。大臣们,你们道貌岸然、圣人嘴脸,难道身上就真的一点污点都没有吗?抛开平日里工作之余到各处勾栏里公然鬼混,其他的丑行更是数不胜数。
就以孙沔你为论,就不是个好东西。
孙沔贪财好色。按说只要是男人,就没有不好这两样的,可像他这样出格的也实在不多。总体来说,他做到了到处好色,随地发财,走一路贪一路,从没有落空的时候。
先说财,他在并州当官时,衙门里的吏卒们时常出公差,四面八方,跑得超勤快。却不是为了公务,是拿着朝廷的旅差费,给孙沔贩运纱、绢、丝绸、纸还有药品。这很让人讨厌,不过是当时的风气,几乎每个官员都搞这样的把戏。
同时过百万的禁军、厢军,各衙门的小吏衙役们也就都有了营生,不至于太闲了。
上面的是通例,下面就刺激了。孙沔贪财时是凶狠型的,只要挡了他的财路,不管是谁,都小心着家破人亡。他在杭州当官时有两件事,很有代表性。
首先是继续做买卖,孙沔亲自出马,和一个姓郑的萧山人谈纱的价钱。郑某一时不识官商真面目,出的价很高,而且不还价。孙沔只好怀恨出门,越想越气,决定来个狠的。他派人去查郑某的案底,辛勤查账之后,果然查到这人偷漏了税。
把柄在手,价钱好说。可惜郑某把事儿看得太轻了,孙沔要他的纱,更要他的命,一点偷税的勾当,就把他发配到了别州,家产全部充公!
这还是勉强说过去的事,毕竟郑某自己手脚不干净,给孙沔留下了整人的理由。下一件事,就纯粹是恶人本性,卑劣的畜生行为了。
杭州自古繁华,地杰人灵之外,还相当的有钱,民间总有些稀奇古怪的宝贝偶尔曝光。杭州市民许明就藏有100颗成色极好,浑圆硕大的珍珠,以及一幅郭虔晖所画的《鹰图》。地道的奇珍加古董,让懂行的孙沔大流口水。为了得到这两样东西,孙沔大动了一番脑筋,想出了一个层次分明,超级混蛋的计策。
东西有两样,要各个击破。谨防许明一时冲动,把宝贝毁了,来个玉石俱焚。他由自己的小舅子出面,先去买珍珠。100颗罕见的大珍珠,他出价32000钱,也就是320贯!几乎连一颗珍珠都够戗买下来。但是竟然成交了。
这就是手段的高明。孙沔摸准了许明的心理,许明爱珍珠,更爱《鹰图》,总想着花些代价把瘟神打发走,所以对珍珠就不会认真。
珍珠之后,《鹰图》就更成了许明的命根子,孙沔知道得玩狠的了。现在请朋友们掩卷默想,要用什么样的手段,才能让许明乖乖地交出宝贝,不得不屈服呢?
千年之后,都觉得匪夷所思。孙沔居然查到了许明小时候有个乳名,叫“大王儿”。这就是罪,一介平民,僭越称王,你想造反吧!
许明被刺配充军,《鹰图》顺利落到孙沔手中。许明直到孙沔调离杭州之后,才在营牢里自断一臂到提点刑狱使司喊冤,得到释放。
以上是孙沔的贪财事例,下面看他的好色。
孙沔之好色,达到了兼收并储,来者不拒的程度。具体的表现就是无论是良家妇女,还是军营官妓,只要他看上了,就在劫难逃,终究到手。
他在处州当官时,某次外出游玩,偶遇一位名叫白牡丹的女子,突然心动,不可抑制,于是诱(史书原字)回官舍,如此这般。这是第一件,第二件发生在并州,他在上任的路上,居然公开接收妓女一路同行。
以上考虑到被害方的身份,妓女,还有白牡丹这个名字就不是正当职业者,孙沔的行为只能归纳到行为不端上,小小的风流罪过。那么请看下一例。它也发生在风景如画的杭州。
杭州自古多美女,西湖边上总关情。孙沔曾经日夜都在那里流连。结果他就看到了一位姓赵的超级美女。可惜名花有主了,她许配给了一个叫莘旦的人。孙沔开动脑筋,要怎样才能不合理但绝对合法的把赵美女据为己有呢?
办法永远都会有的,只要你有权力和欲望。孙沔先从莘旦的家人下手,他借口莘旦的母亲与和尚私通,把她抓到官府。又指派官妓把赵美女的妈妈看住,另换一套面目,充当救命恩人,把赵MM带走,从此日夜厮守……这就是在张贵妃葬礼上大义凛然,主执正义的枢密副使孙沔孙大人的真实本色。
这样的人居然能位极人臣,还动辄以仁义道德自称,真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。其实也不止是他,全宋朝官场的大臣们,几乎全体手脚都不干净。就以这次葬礼风波为局限,把出风头的几位都详述一遍,就可以看到盛世间的士大夫一族是怎样的嘴脸了。
下一位出场的人是宰相陈执中。前面说过,庞籍下野之后,梁适升相,但他没有资格做独相,很快皇上的老师、恩人陈执中回朝,分了他一杯羹。这时孙沔突然当众秀道德,撂了挑子,危难中陈执中顶了上来,坚决支持皇帝。
枢密副使不读哀册,那么宰相来读。陈执中让张贵妃的葬礼骤然升格,比之前的待遇更高了。葬礼圆满结束,皇帝对恩师充满了感激之情,大臣们恨不得骂死这个老牌的墙头草。
这是士大夫之间的仇视,作为现代人,可以忽略,因为陈执中毕竟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,按照宋朝的为官之道做人。我们所要看的,是他作为一个“人”,做出了什么样的勾当。
半年之后,他家里出了件事。官方资料记载,是死了一个婢女,名叫迎儿。遍体鳞伤,体无完肤,开封府调查,是被活生生打死的。案发过程,有两个说法。一,是陈执中亲自动手,把婢女打死;二,是他一向酷虐的爱妾张氏殴打至死。
官方结论,不管是哪一种,陈执中都有不可推卸的现任。
还有另一个版本的记载,出自司马光的私人笔记《涑水记闻》,死的不是一个婢女,而是三个。迎儿当年只有13岁,只是个女童而已,不知犯了什么过错,在张氏的鼓动下,陈执中亲自动手,毒打多次,寒冬天气里,赤裸捆绑,关在黑屋子里,直至冻饿而死。另两个女婢一个叫海棠,另一个不知名,海棠被打死,无名的那个被剪成秃发,自己上了吊。
这是堂堂宰相府,知礼读书家的做的事吗?!陈执中对外恭谦礼让,对谁都客客气气,想不到背地里居然这样残忍刻毒!
事情曝光了,陈执中被御史台弹劾,停职回家待罪。从当时和现在人的普遍意识里,他这就算完蛋了。想想看在宋朝的仁宗年间,居然出了这样的事,除了法办之外,还有别的答案吗?结果是有。那是个封建年代,人和人就是不平等的,现代的人权意识,在那里没有市场。
哪怕是仁宗皇帝再仁慈,也没法把一届宰相和几个丫鬟使女的性命等同起来。他犹豫,这只是私事,最多不过是丑闻,难道就此罢免老恩师,甚至法办他吗?
他的这种犹豫,直接导致了司法部门对陈执中案件的审理力度。尽管御史台全体出动,不断弹劾,陈执中的宰相头衔岿然不动。直到仁宗朝第一位吵架王、弹劾王欧阳修回京。
庆历年间被贬到外地的大才子欧阳修终于回来了,他的职务被安排到一个非常对口,非常称职的地方,是两制官里的翰林学士。清闲又富贵,可他待不住。第一时间地冲进了漩涡,不遗余力地打压陈执中,不把这个貌似忠厚,极端无耻的斯文败类打倒斗臭,他誓不罢休!
至于为什么这么冲动,他自己知道,全宋朝也都知道。那涉及到另一个巨型丑闻,间接地就由陈执中制造。
庆历新政时欧阳修比范仲淹等主角还要出彩,他旋风腿冲天炮打遍宋朝每一个角落,让几乎全体官员都灰头土脸贴上小人的标签。这样做是有报应的,牛人出牛事,仁宗朝、甚至北宋第一丑闻就落在他的身上。
事情是这样的,欧阳修的二妹夫早死,妹妹带着女儿张氏到他家生活。欧阳修把外甥女养大成人,嫁给了自己的远房侄子。可是他的教育力度明显不够,这位张氏女孩儿有个坏习惯,她喜欢外遇,和丈夫衙门里的办事人员有了暧昧关系。事发之后,由当时的开封府尹杨日严办理。
杨日严在历史里籍籍无名,在欧阳修的心里也就没了印象。他狠扁过的人实在太多了,数都数不过来。这位杨先生曾经在益州任上贪污渎职,被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弹劾丢官。有怨报怨,有仇报仇,本来是小一辈的龌龊事,竟然联系到了老一辈的欧阳修身上。
审理报告上说,张氏供认,当年在欧阳修的府上,她和舅舅通奸,而且有银钱往来。此报告一公布,天下立即大哗。天哪,这是乱伦,最让人不齿,最恶心的一种丑事,居然发生在了当代才子之冠的欧阳修身上!
会是真的吗?普天下的人都在问,官场上却一致认定。真的。理由有二,第一,欧阳修有前科,这人风流好色,早年时就和官妓鬼混,留下了好多精妙绝伦的诗词,他推都推不脱;第二,他变卖了张家的宅院,钱都归为己有。这有契约为证,根本无处抵赖。
在当时,舆论说什么的都有。有认为欧阳修被陷害,这是打击报复。不能说有银钱往来就是通奸吧?亲戚家互相借贷,这再正常不过了。都是杨日严这小人在从中搞事。另一种占绝大多数的说法是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,种种迹象表明,欧阳修就是个乱伦犯!
结果他就被贬出京师,外地反省了。要指出的事,那时的宰相就是陈执中,倒修事件中,他最差也是个默许者,所以欧阳修把他恨得死死的。这时丑闻轮流转,今年到陈家,还不快意报复?
欧阳修出手,是北宋仁宗年间最可怕的弹劾武器,堪称战无不胜,弹无不倒。从战绩来说,别说是软柿子陈执中,就连名垂千古,铁脸无情的包拯,都不在话下。
陈执中倒了,他熬过了整个御史台的狂轰乱炸,连御史中丞孙抃为了他辞职不干,要同归于尽都安然无事,可是欧阳修一到,立即被赶出京城,到亳州去反省思过。
事情到这里可以暂时告一段落。总结一下,在一般的史书中,这段时光里宋朝发生的都是一些零碎的琐事,没什么需要重视的,也没法归纳出什么。紧接着它就进入到了至和、嘉祐年间(1054-1063年),那时就更太平,更祥和,更琐碎了。根本没法整体说事。
但是仔细研究,我发现不尽然。上面所说的这几件事,正是宋朝,至少是仁宗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仁宗朝在此之前,尽管外患内乱不断,可是在赵祯的领导下,一切都平稳有序。在张贵妃死后,赵祯的心灵和身体都发生了巨大变化,这直接导致了他的施政纲领,还有领导力度。
宋朝开始变样了。
说张贵妃之死,本是一件小事,除了生死两皇后的名分很重叠,对曹皇后一再地轻视不敬之外,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?有的,自古以来,领导人的配偶对领导人的影响非常巨大,连带着对国家的运作也有波及。远的例子,比如唐高宗李治,如果他的身体一直健康,怎么轮到武则天批奏章,管国事?近的说刘娥,赵恒晚年神智昏乱,没法办公,她才走上了前台。再近些说慈禧,她的丈夫也是病死得早,儿子还太小,才轮到她当政。
综上所述,已经很明确了。如果这几位女强人的丈夫一直健康正常,她们根本没有走出后宫,打家劫舍的机会。证据就是她们丈夫得病之前,她们没一个敢挑事的。
具体到赵祯的身上,就是张贵妃死了,他必须得找新的女人。这不仅是生活的需要,更是工作的需要。他得给宋朝的百年基业生出个继承人来。于是女人多多选,出现了10位得宠的嫔妃,号称“十阁”。10个啊,这样的工作力度,让赵祯很快出现了健康问题。
先是无精打采,渐渐地病情加重,突然间昏迷不醒,长达3天。之后健康每况愈下,再也没有振作起来。这样导致了两个后果。
1,传说中的盛世出现了。国家随遇而安,官员随国而安,和他的身体一样,平稳高于一切。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,做到了与民休息;
2,传说中的名臣出现了。皇帝病倒,国家还得有人管理,一大批的名臣冒了出来,他们既要照顾好皇帝,又管理好国家,这让所有朝代的臣子们钦佩,造就他们不灭的英名传奇。
具体的发展过程,就从陈执中下课开始。他和梁适都走人,中书省大换血,上任的是文彦博和富弼。其中的富弼和稍后上任的权御史中丞包拯、任经筳侍讲的大儒胡瑗,以及翰林学士欧阳修,并称为“四真”。即富弼是真宰相、欧阳修是真学士、包拯是真御史、胡瑗是真先生。
至于文彦博,谁让他的仕途那么悠长,中间起伏不定,到评定四真的时候,他又潜水了,头衔被暂时剥夺。
四真当朝,是宋史里少见的盛世传说,被后世一再传颂,那么就从他们说起吧,看看这段时光都发生过什么事,谁做了什么。四人之中,胡瑗首先剔除在外。这位真先生是儒学宗师,除了学问高深之外,最让人敬佩的就是道德隆重。人家从来不趁着和皇上挨得近,就什么都讲,什么都掺和。
于是经书之外,没有天地。胡瑗独善其身。
包拯暂时也没有戏份出场,他之前弹劾张尧佐用力过猛,还在修养复原中。余下的就只有富弼、文彦博、欧阳修了。这三个人一贯活在风口浪尖上,可惜富弼也要除去,他真的成了仁宗朝的“真宰相”了。他创造了一个纪录。
高洁无瑕,片尘不染。终其一生,再没有任何人弹劾他。
这真是破天荒头一个,连范仲淹都做不到。其原因是什么呢,此人变了。被夏竦的谣言击中,贬出开封之后,富弼的心灵起了极大的变异,让当年那个为国为民热血沸腾,与契丹交涉不惜性命,谈改革不顾身家的真汉子变成了宋朝最经典的执政官,成为“真宰相”。
这个心灵转变,除了悲哀,或者成熟了、腐烂了之类的评语之外,其转变的原因、过程,都足以成了宋朝不断没落,走向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那个冬天的缩影。帝国之亡,实亡于人心之没落。
说得远了些,五人中只剩下了欧阳修和文彦博。这两个人都是新回京师,能力和风格让他们立即就成为风云人物,其开端就是困扰了宋朝快八年的黄河水灾。
八年前黄河改道,按中国5000年里只有8次的概率,可以说是近千年一遇的大灾了。面对滔天的洪水,百万流离失所的灾民,还有巨大的损失数字,宋朝的举措是相当认真的。
前面说过,两位前宰相贾昌朝、丁度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如贾氏的恢复故道,商胡溃堤,就在商胡复原;丁氏的从长计议,先疏通河水,看准流向之后再动手的缓期救灾。怎样决策,慎之又慎,认真的程度达到了连续思考了4年。
4年后,公元1051年七月,黄河在大名府馆陶县郭固口又决堤了。
这次决堤就像是得了癌症之后又发了次小感冒。尽管癌症很要命,可是感冒来得更现实,让人没法不先治它。5个月之后,郭固口合拢,但是仅仅限于合拢。水道内淤泥堆积,越来越厚,水面被抬高,随时都有漫过堤坝,再次崩溃的危险。
说到这里,就让人奇怪了。宋朝是中国历代最有钱的王朝,就以贾昌朝恢复故道的办法,号称最废钱费力,也不过就是1000万贯钱,10万民夫而已。参考一下历次战争的花费,就该知道,这不过是宋朝的九牛一毛。那么拖来拖去的,到底因为什么?
谜底还得再等一会儿揭开。进入至和年间了,文彦博和富弼当上了宰相,这两个人不管真实面目与传说中有多大的差距,为国为民的好心肠还是有的。他们广泛征集意见,整理出了一个新办法。据专家判断,一旦实施,就能以最小的工作量达到最完美的治水效果。
――六塔河方案出笼。
六塔河,在河北省清丰县的六塔镇,与黄河相通,却不入海。具体的办法是,把六塔河的河面河道加宽挖深,来容纳黄河泛滥的洪水,这样上游的商胡地段就会得到缓解。水流减缓之后,商胡的崩溃点就可以相当容易地塞住,同时约束河水按故道流淌,进入大海。
提出这个方案的是宋朝的河渠司主管李仲昌。从身份上讲,这是位专职专管的治水专业人员,说的话应该靠谱。从纯技术上分析,也很有道理。以六塔河分水,可以让商胡口的决堤处减缓灾情,容易堵塞。尤其是一旦成功之后,六塔河的后期作用更是巨大。
它可以成为黄河的永久性分水道,不管在什么时候,都能保证黄河的崩溃系数维持在之前历代最低的程度。多好的办法,立即就把文彦博和富弼给迷住了。他们联名上报给皇帝,请批准,立即实施吧。
且慢,欧阳修有话说。
新任的翰林学士看上去义愤填膺,心里有好多的话,都快把他憋爆炸了。他一口气写了几千个字的奏章,把前面提出的3种治河方案都批得体无完肤。
第一,关于贾昌朝的恢复故道,欧阳修指出,也不想想为什么近几十年来河患不断?就在于故道泥沙淤积,已经积重难返,根本就不可能再恢复了。一定要逆天行事,难道与天斗,真的其乐无穷?
第二,关于丁度的从长计议,就是宋朝版的官员不作为罪行。从长计议,8年了够长不?你有什么计议结果请尽快出现,难道国计民生的重要,都维系在您不定时短路的脑子?
第三,六塔河计划。这是最让欧阳修不堪忍受的,他实在是怀疑这个世界是怎么了,难道一个个国家大臣都成了白痴加废物?六塔河,只是一条40步宽的州县级河流,它能有多大的容水量,想让它给中国北方第一大河减水……你们的脑子进水了吧?!或许每个脑子注水100吨,黄河就安静了!
综上所述,每一条方案都不成立。欧阳修在愤怒之余,也提出了自己的办法。他建议派真正懂行的水利大臣到黄河的下游去,别再只把目光盯在商胡、郭固口等上游危险地段。把黄河的入海道路修好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
水往东流,渠成自畅。这才是根本正路!
又一个方案产生,欧阳修把整个朝廷吓了一大跳之后,又把希望给了他们。平心而论,他说得都在理,尤其是关于六塔河的分析。无论如何,40步宽的河面就决定了方案的先天不足。
那是给中原第一大河减水!
从理论上讲,只要六塔河的容积不够,黄河水势必倒灌回故道,上游的压力会急剧增加。欧阳修断言,那时上游必溃。
奏章交了上去,他和全天下人开始了等待。强调一下,这就是欧阳修的力量,他的文章在年轻时代就风行全国,20多年以后,已经是宋朝当时公认的文学泰斗。天下第一大家,随便写点什么都是万众瞩目,这种影响力谁敢忽视?
但真就被忽视了。欧阳修怎么也搞不懂,无论是治河的见解,还是文字的功力,还有他和富弼的交情,都注定了他将扭转治河事件的乾坤,可偏偏就被扔进了废纸缕里,没人去看。
李仲昌的六塔河计划被提上日程,变成了治河主旋律。
欧阳修再一次失败了,他像惯例一样的被主流官场所抛弃。这种遭遇从一些角度上看,是很好玩、很可笑的,他怎么总是出丑啊,干生气没办法。可换一种角度来看,就会别有一番感触。这件事起码潜藏着两个真相。
第一,历尽官场风霜,唯一没有变的人只有欧阳修。以还活着的庆历新政的“君子党”为限,富弼变了,韩琦变了,那些曾经激扬奋发的青年馆阁人员更是找不到踪影。只有欧阳修以前什么样,现在还什么样。这让他继续在官场上出丑,总是当异类。
可“道之所在,虽千万人吾往矣。”他坚守着从青少年时起就抱定的信念,虽然迂腐,哪怕不合时宜,他在物欲横流的官场上永远都保持着一个书生的本色,从来都只做他自己。这难道不是极端难能可贵的吗?
第二,他这次失败的原因也很简单。治河,至少在古代,从来都不是一件民生工程,而是一种政府工程。欧阳修与庆历故人们渐行渐远,不与同流,属于无党派人士了,那么自然就不会再有人重视他的意见。
三种意见,哪种都有幕后的支持者。贾昌朝的背后是陈执中,李仲昌的背后是文彦博和富弼。丁度的稍好些,因为他实际上根本就没提出具体办法。
这样一件大工程,在谁的治下成功,都会变成他巨大的政治资本。就比如贾昌朝的恢复故道法,他和陈执中都处在下野状态,如果被采用,现任的文、富二人脸往哪放?一旦治河成功,功劳算是谁的?
贾和陈立即就有了东山再起的声望。
围绕着最后利益归属的问题,巨大的水灾危害变次要了。双方都用尽了手段,来打压反对对方的方案,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的意图得逞。最先发难的人是贾昌朝。
贾昌朝的资历很高,在庆历年间从右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,一路升上了参知政事,再到枢密使。直到新政开始,才被范仲淹、欧阳修赶出朝廷,也就在那时和富弼结成了冤家。这时他的运气非常好,本来国家重大决策,大臣们除了写奏章,搞辩论之外,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可是机会突然降临,让他能使盘外招了。
事情发生在那一年的春节时。宋朝的至和三年(即嘉祐元年,公元1056年)。正月初一,是一年中的大日子,这一天百官齐集大殿,盛装排列,庆贺元日大朝会。谁也没有料到,就这在这个时刻,出大事了。
只见两边的内侍把殿上的帏帘卷起,露出了帘后的皇帝,大家正要参拜,突然看见皇帝的头向一侧歪倒,随即整个人都倒了下去,皇帝昏倒了!
御阶上的帘幕立即又拉了起来,里边人影晃动,一阵忙乱。下边的百官们惊慌骚动,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样了。直到好一会儿后,帘幕重新拉开,大家又看到了熟悉的仁宗皇帝,他又能坐直了身子,与大家遥遥相对。
当天大臣们勉强压住心里的恐惧,向陛下依次行礼,徐徐退下。回去的路上,每个人都在想,皇帝到底怎么了,明天还能照常登殿理事吗?
明天不行,宋朝的年假直到大年初五。初五日上班,大家接着朝贺,而且有新节目。宋、辽两国乃兄弟之邦,每年春节,辽国都要来给哥哥拜年,于是按惯例,初五这一天,要在紫宸殿设宴,款待辽国使者。
全体朝臣都提心吊胆,要是陛下再当众玩次晕倒,这名声可就传出国界了。真的要变成“晕君”?他们多虑了,皇帝可以晕倒,不过得20年一遇。大初五的,仁宗有新花样。
简短节说,所有的排场重复了近100年,都成惯性动作了,什么错也没有,直到宰相和皇帝面对面。最高潮的桥段到来,得由宰相手捧酒觞登阶近距离为皇帝贺寿,并请皇帝发表新年讲话。
就见新年有新气象,陛下坐得稳稳的,下面群臣站得静静的,皇帝突然说,“不高兴吗?”(不乐邪?)文彦博一下子就愣住了,这句话什么意思?是陛下看我不顺眼,还是对宋、辽两国的邦交有了新的意向,要在朝贺日给辽人不痛快?
脑子里电光火石般地闪烁答案,可是都觉得不靠谱。理智告诉他,最贴近的答案就是皇帝还在晕,说的是病话。他作为宰相,就别跟着晕了。于是闭嘴,马上上菜,开吃!
当天的宴席上仁宗一直稳稳地端坐着,没再说话,甚至没有表情。直到典礼结束。大臣们一把冷汗拎着,总算松了口气。不过再次回家时,心里就都有了个问号,皇帝是病好了,还是更重了?
这事儿还真不好讲,瞬间晕倒和语无伦次,哪个都要命。
第二天才真正要命。中华上国,礼仪之邦,初五日是迎接辽使,初六还要送行。仍旧还在紫宸殿,原班人马继续喝。辽国的使者正在上殿,走到庭中央时,皇帝突然间喊了一句话:“速召使节上殿,朕几乎不相见!”
满殿的大臣集体一哆嗦,您是今天失忆,还是昨天梦游,把一整天的事儿都忘干净了?眼看着宋朝在外国人面前保持了近100年的体面就要倒塌,在场的官员们瞬间开始配合,兵分两路,台下面由宰相出头,把辽国使者拦住,直接往外拉。
理由是皇上高兴,昨晚上喝醉了,今天由大臣们在驿馆里设宴,咱们换台喝。
这时台上面一片忙乱,内侍太监们不由分说,把皇帝架起来就走。那架势倒真跟宰相说得差不多……